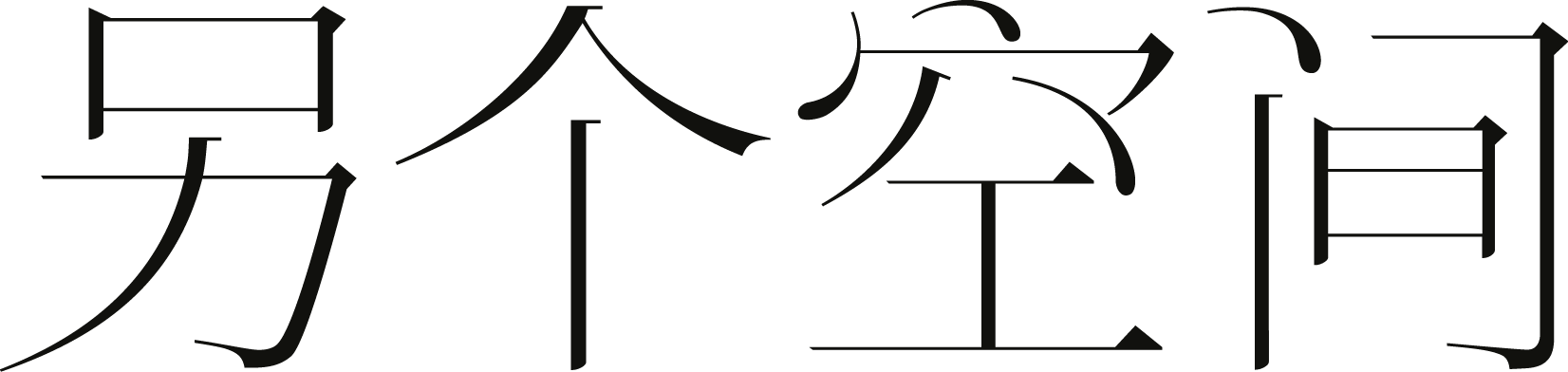寻找故土 —— Kurt Tong 在香港与中国探索记忆和身份
电话那一头,Kurt Tong 的声音越来越兴奋,他在解释作品中的私人情感和生活经历,言语简单直白。此时,伦敦正享受着罕见的午后阳光,香港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Tong 刚把孩子送上床。他说晚间 Skype 通话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因为关系网很国际化,他定在奇怪时间点的采访比去欧洲的次数还多。这不单是因为香港艺术圈的限制性,更多是介于摄影师本人辗转各地的生活经历。70年代,他出生成长于香港,13岁时和兄弟一起搬到英国,在寄宿学校学习。大学促使他环游欧洲、美洲和亚洲,并在印度停留许久,为一家非政府机构工作。在那段不断探索新事物的时光里,他通过相机捕捉自我之外的世界。”我是从那时开始拍照片的,” Tong 说道,”很投入,做了一个长期项目,还拿了西班牙的一个奖,这个奖为我打开了一些门。当时我觉得 ‘ 这可以发展成很棒的职业道路!’ 十四年后——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摄影当然不是错误,他只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2006年,Tong 回到伦敦攻读纪实摄影硕士学位,学习帮助他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追求。”开始时,我认定 ‘这就是我想做的,’ 结果毕业时我一点也不想做纪实摄影,”他说。”之前我经常旅行,一直觉得自己触及了不同故事的深层意义,但读研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记录过比表面更深层的内容。从那时起,我的作品开始从自我和我周围的环境出发,探索已知,而不是漂洋过海去看最基本的东西。”
带着这样的新目标,Tong 开始了一段直面复杂问题的旅程——身份、记忆、归属——他将三者关联,探索自己分割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家庭历史。他的部分发现已在 《女王,主席与我》 摄影项目中以家庭照片和文字形式得到了美好呈现,中心问题即是:我有多中国?或者其实是:我是谁?
在他的个人新展于香港光影作坊 10月14日开幕前,我们和这位摄影师谈了谈他追寻故乡的经历。
2012年,你在与 Jonathan Blaustein 的 aPhotoEditor 采访中说道:”二十多岁时,我以世界公民自居,在印度和东欧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不论去哪,我都在家。直到我女儿出生,我才觉得自己又成了中国人。” 你觉得这是心智成熟过程中自然的变化吗?
我不能代替所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的确是在女儿出生后才有了这种感觉。她是混血——我妻子是苏格兰人——当时我们又住在伦敦,所以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义务教她如何去做一个中国人。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想教她而想更好地理解做中国人的含义。
你也是在两种文化中长大的,会不会觉得在对女儿进行教育前还要进行一番自我探索?
她出生时——我们是在说十年前的事了——我的中文口语还不是很好,并且已经离开香港快20年了,所以我并不清楚来自香港意味着什么,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我很需要探索这些问题,而且研究得越多,就越想做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
在英国那么多年后再次回到香港的感受如何?
蛮困难的。我们是2010年回来的,我开始了《女王,主席与我》的摄影项目,全身心地在香港溯源。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不会待很久,所以觉得不难。我只要知道怎么在香港生活就可以了,但不需要去交朋友。我不需要再一次扎根。但2012年我们回来时买了猫,所以也就是准备长期居住了。对,这就很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定要去交朋友,不论什么时间都要住在那儿。回到自己儿时成长的文化中,努力再次融入它,这是有文化冲击的。
你的早期作品,譬如《人民公园》和《回忆、梦境;间断》探索了我们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特别是大脑对记忆的改变。是什么引起了你对这些主题的兴趣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家里的老照片,它的审美和造型。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人们描述这些照片的方式,当我让亲戚们谈谈这些照片时,他们每次讲的故事都不同。这其实就是我作品的起点——人们如何将照片变为回忆的载体,如何每次都有所不同地解释它们。
既然你对家庭照片很感兴趣,那你现在会自己做家庭相册吗?
会,但不是从艺术角度去做这件事,我每年都会很传统地拍很多照片,洗出来做成相册。
我家也会这样,我们有很大的存档,里面有每个人的照片,一直回溯到我外祖父母的童年。真的很棒。当你记不清过去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有这样的时光记录很重要,因为照片总能让你想起些什么。就像你说的,记忆不准确,但你可以重构过去。
在做家庭相册项目时,我意识到人们记住的只有最不好或是最好的时刻,不痛不痒的回忆都消失了。所以人们总会说”哦他做了一件特别坏的事”或是”他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而从来不是”他就还行。”
你是如何与这种”篡改”过程建立起关系的?
我可以就具体的展览来讲一讲。在《回忆、梦境;间断》里,这是一种实体考验的关系。我开始以非常直接地方式拍摄我女儿的公园,但这些图像总是不尽人意。接着我又在科学杂志里读到一篇文章,讲回忆是构成的,大脑会将它们分裂成积木般的碎片。我们只能记住一切的40%。每次我们提起一段往事,大脑都会补充剩下的60%。我想复制这个过程,所以我真的摧毁了底片,再尝试着从中得到一点信息。接下来在做《女王,主席与我》时,人们都说:”你有这样的家庭历史档案真好啊!”但我总会告诉他们,一半的故事都不是真的。在开始拍照前,我就已经花了八个月时间收集照片和故事,每个故事又都有好些不同版本。所以最终成品其实只是我的版本。当我展示作品时,重点并不在于书本身。我在画廊里建了一个中国茶馆,观展的人群可以坐着看照片。那里还有送茶的侍者,所以他们会边喝茶边读我的书。我发现他们都会在读到第三章时放下书开始讨论自己的先辈。真的每次都是这样!当初做完这本书时,我很担心它会因为全是关于中国移民的内容而太过香港。但其实它能引起跨文化的共鸣。我记得开幕那晚,一个葡萄牙男生走到我跟前和我说:”我爱这本书,它就是我的故事!”我听到这话时有些困惑。不过很快他就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出生于莫桑比克,殖民结束时被迫搬回了葡萄牙。我意识到,整个19十九世纪,过去的150年,都是关于移民与穿越边界的历史。这个作品的真正意义其实在于发生在茶馆里的对话。回到你的问题,我想我的工作就是要促使人们去思考、认真探索自己的记忆和历史吧。
你最近的作品《唐水黄土》是通过旅行和摄影对你失去的故乡——中国——的一次探索。你说你与中国的地貌有一种情感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此之前的四个作品都关乎我如何重新做回中国人,但《唐水黄土》的出发点是好奇自己能不能将中国视作一个国家、一片土地,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系。我是从拍摄爷爷和外公在中国南部的家乡开始的。他们一个来自渔民人家,一个是大地主家的儿子。我拍了很多他们老家的照片,但我无法在这些照片中找到联系,它们不是很有趣。我意识到自己无感的原因是他们都在100年前就离开了中国。一个120年前就走了,想要寻找更好的工作,另一个在1949年时离开了,因为他是地主。于是我问自己:”如果我不能在这两个地方找到我的中国,那我去中国时应该寻找什么呢?”我便开始思索自己对于这个国家视觉语言的理解,发现自己是有预想和期许的。我小时候从没去过中国,27岁时才第一次去。我青少年和少儿时期关于中国的想象都来自于一部日本拍的关于丝路的纪录片(NHK的《The Silk Road》)。在我的意识中,中国看起来该是片子里那样,非常浪漫,云雾缭绕,大地延就这样伸开来。我去中国时去了很多地方,每当我看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都会感觉到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因为那就是我脑海中的中国。
那是你所认识的景象,在出发之前就有的回忆。
对,那是我当时对中国的理解,一个辽阔,多雾,沙丘延绵的地方。
同时你也感觉到自己与周围人群的格格不入。
是的。去中国也是一种文化冲击。我初到香港,带着想象去中国时,很多原有的想法都被现实否定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香港长大,我们总觉得比大陆人高人一等。但当我开始在中国南部和人们交朋友时,这些隔阂都不再了。我能和南方人交流得很好。但每次去北方,那又是种新的文化冲击。
是的,南北差异还挺大的,像在两个不同国家旅游一样。
没错,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原来中文并没有特别好,但到香港之后就一直在学,能在南方和人聊天。南方口音我是能听懂的,但一到了北方,我就一个字都听不懂,简直刷新了我在中国不同地区受到的文化冲击。如果你按照序列看完《唐水黄土》,会发现照片里的人像越来越大。每次接近他们时我反而会觉得更孤独。因为他们一旦想和我说话,就会发现我其实不是本地人。作品的陈列是这样的:我离他们越近,你就会更频繁地看到人像,人像会越来越脱离于我,脱离于彼此。他们总是看着手机,而不是看着彼此。
你在《唐水黄土》还对底片进行了物理处理,比如把它们放在你的鞋子下面或是浸泡在海水里。你是怎么想到要这样做的?
在做完《回忆、梦境;间断》之后我就一直会对底片进行特殊处理。我享受这个过程。我一直都觉得只拍照片限制很大,所以我和自己拍摄的相片保持了关乎触觉和互动的关系。这是个很自然的习惯。
你有没有在哪个新项目里同时用了这两种创作方式?
有。我的新作品着重尝试使用了混合媒介。 最近我其实在给下一个关于自梳女的作品打米。这是一个曾经从事丝绸业的女性群体。自古以来,女性在中国的地位一直都很低下,但这个区域有不少丝绸交易,女人可以赚比在其他地区更多的钱,所以也更加独立。十七世纪末丝绸业衰败时,她们很难再赚到钱,但依旧遵循以往的生活方式,不受男性指使。所以一到该婚嫁的年龄,她们就发誓终身不嫁守童贞,把头发按照特定的方法梳起来,穿一种特定的衣服。一旦这样做了,她们就可以离开家乡去赚钱。如果你去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就会看到不少她们梳着长辫,穿着白色宽松上衣和黑色长裤的照片。许多自梳女起誓后都是被逐出家门的,于是退休后,她们一起凑钱造房住。中国南部有许多这样的房子,她们在那儿养老。关于她们的作品我已经做了很久,但后来发现太泛,太没深度了,所以现在改成了只讲一个人的故事。
那米是用来干嘛的呢?
她是一个被家人嫌弃的女儿,从小不能上学,遭受虐待,整个成长环境都不友好。但五十年代大饥荒时,全家人都挨饿,她在香港工作,就会每个月回去给他们送食物,一家人这样才活了下来。所以我在用米做一些雕塑。我和这个项目还是蛮有感情联系的,《唐水黄土》关于错接和缺少联系的作品,但我很珍惜它。我不爱它,但那似乎就是它的意义。倒是这三个月前开始的作品现在发展得很不错。我很兴奋。
你用”我究竟有多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开启了《女王,主席与我》系列作品。所以你找到答案了吗?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蛮清楚的。香港人从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总说我来自香港。20岁时,我周游世界,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但做完这些作品后,我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骄傲。我觉得香港人对做中国人的认识总是非常现代,非常共产。但现在我认识到,我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因为它有6000年的文化和历史,而不仅仅是过去50年间发生的事情。